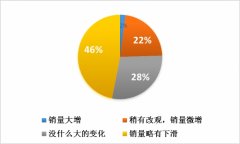从当前态势观察2016年的全球增长格局,总体状况预计会是:发达经济体在温和复苏的路上,而新兴经济体总体继续调整。然而,与前几年仅仅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分化不同的是,现在新兴经济体集团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在新兴经济体整体继续放缓的大背景下,印度、墨西哥、波兰这三个分别位于不同大洲、增长状态迥异的新兴经济体,自2013年见底之后,也已经走上了持续复苏轨道。
新兴经济体增长态势的内部分化暗示着,单纯全球经济低迷这个被援引了8年的大背景,已越来越无法作为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令人信服的托辞。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间的结果,各个经济体不同的政策选择,正在导致彼此之间增长路径日益分道扬镳!
笔者的数据分析发现,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序列,几乎严格遵循了“谁先贬值谁先复苏”的“艾钦格林-萨克斯次序”。
而新兴经济体也清楚显示了类似的规律,目前已陷入衰退中的巴西和俄罗斯,其本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在2007~2012年间一直属于新兴经济体中最高的;而到了2012年之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开始超过它们而独步天下,并非巧合的是,我国宏观当局虽然尝试了除汇率之外的种种药方,但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挥之不去。
如果说产能过剩抑制了经济复苏,那么,在2002~2007年那一轮流动性过剩所驱动的全球过热景气周期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齐头并进,面对国际贸易增速不断加快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高涨,又有谁真正有定力而未干过过度投资的事呢?而今,毕竟七年过去了,调整的时间已经不短。
人口红利消退的说法,相当流行,且为更多象牙塔内学者所推崇。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中国过去的劳动人口增速和经济增长数据,就不难发现在5~10年这样的时段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虽然不排除在更长时段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密切),特别是在1997~2002年通货紧缩的几年中,中国劳动力人口增速突然爆发式加速,但经济增长却异常低迷。
看来,最后只能求助于所谓生产率下降之类的解释了,但正如首创全要素生产率(TFP)概念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RobertSolow)所坦承的:其只不过是度量了我们的无知。笔者没法也无意于否认存在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可能性,但却不免要提出疑问:既然承认了效率的下降,那么,在2013~2015年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反倒还加速升值的合理性何在呢(要比2005~2007年和2010~2011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时期高得多)?
种种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决定了中国经济探明底部还需时日,2016年仍然处于政策的摸索期,摸索中的政策最终必然会呈现出强烈杂糅或“鸡尾酒”的特征。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