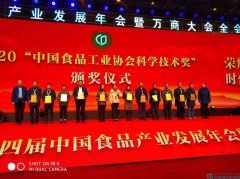《商业价值》上曾有一个案例,介绍的是1948年林彪在战场上利用大数据的故事:
说林彪从带兵开始,身边就有个本子,每次打完仗,他就把战果记在上面,不厌其烦。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以此为乐。
辽沈战役打响后,无论战情如何紧急,多么疲惫,林彪依然每天坚持听军情汇报,而且要求很细:俘虏要分清军官和士兵;缴获的枪支要统计出机枪、长枪、短枪;击毁的和还能使用的汽车要分出大小和类别,每份战报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枯燥数据。
一天深夜,值班参谋正读着一份遭遇战的战报,林彪突然叫“停”。他问周围的人:“刚才念的那个战斗的缴获你们听到了吗?”周围的人满脸都是睡意和茫然,因为像这样的战斗每天都有几十起,只是枯燥的数字稍有不同。
林彪见无人回答,便接连提出3个问题:“为什么那儿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他的战斗略高?为什么那儿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他的战场略高?为什么那儿俘获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一般歼敌略高?”人们还没来得及思索,林彪已指着军用地图说:“我猜想……不,我断定!敌人的野战指挥所就在这儿!”随后,林彪命令全力追击从该处逃走的敌人。敌军首领廖耀湘刚刚还在庆幸自己在意外的遭遇战中幸免于难,很快就发现被漫山遍野的解放军团团围住……
这个案例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利用数据可以进行形势的预判,无论是在现实的战场上还是如今硝烟弥漫的商场上,大数据的作用都不容小觑。
什么是大数据?
大数据(big data),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资讯。
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便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大数据热情地赞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不过,大约从2009年开始,“大数据”才成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的流行词汇。
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产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以往大数据通常用来形容一个公司创造的大量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而提及“大数据”,通常是指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即通过收集、整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数据,对其进行分析挖掘,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最终衍化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那么,所谓的“大数据”究竟有多“大”?
一组名为“互联网上一天”的数据告诉我们,一天之中,互联网产生的全部内容可以刻满1.68亿张DVD;发出的邮件有2940亿封之多(相当于美国两年的纸质信件数量);发出的社区帖子达200万个(相当于《时代》杂志770年的文字量);卖出的手机为37.8万台……
然而,尽管我们文中开头就提到过,林彪曾利用数据的分析进行战争的预判,但是大数据应用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对于数据分析在企业尤其是酒类企业的战略规划中的应用显然还屈指可数,寥若晨星。
在2012年,知名信息管理专家、专栏作家涂子沛出版了一本书叫《大数据》,里面提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互联网大国、手机大国(我们的互联网用户是美国的2倍,手机用户数量是美国的3倍),但却恰恰还不是一个数据大国。
涂子沛引用了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胡适的论述,认为我们社会之所以对数据“不敏感”或者“没兴趣”,是因为中国人“凡事差不多、凡事只讲大致如此”的习惯。1919年,胡适写下著名的《差不多先生传》,活灵活现地白描了中国人取道中庸、不肯认真、甘于糊涂、拒绝精准的庸碌形象。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骨子里的中庸思想,才使得我们在大数据的探索和应用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伴随着中国信息化浪潮的快速发展,这一现象正在变化着,而且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
[1] [2]